《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系》:在精神病院上班,是怎樣一種體驗??
網飛最近出演了一部關于精神病患者的高評分原創劇。名字挺溫柔的:《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系》(沒事也沒事)。
時隔五年復出的金秀賢(剛泰飾)在這部劇中飾演一名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護工。他遇到了一個有反社會人格的童書作家,開始了一段“情感治愈”的旅程。

作為故事發生的主要地點之一,——,剛泰工作的地方,與醫院無關,也展現了一些精神病院的內部。
比如周圍會有很多行為怪異的患者。
對著空氣說話,旁若無人的唱歌,或者感覺每個角落都在被監視,都是在監視ta:

他們可能沒有行動自由。
病房關著,窗戶也鎖著。如果你生病了,你可能會被放在床上,并服用鎮靜劑。

病人拒絕吃藥。他們練習各種藏藥絕技(比如假裝把藥射到嘴里,實際藏在手指里),每天和醫生護士斗智斗勇:

影視劇和小說為我們提供了夸張想象的基石。
對于“精神病院”,普通人總是有很多想象和誤解。許多人聽說過嚴重到需要住院的“精神疾病”。情況一定很糟糕。
真正的精神病院是什么樣的?
其實很多心理比較單純的心理咨詢師,出于工作需要,都在精神病院待過一段時間。
我們聯系了、和周,和他們聊了聊咨詢師眼中真實的精神病院生活。
病人的隱私被模糊了。

去精神病院對我來說就像是一次“田野調查”。
我想知道我不知道的。一個人怎么會變成那樣?那些書上寫的癥狀在現實中是怎么出現的?再大一點,可以高密度地看到那里人類的苦難。
那段時間精神病院就像“另一個世界的9又3/4站”,我沖過去,然后我就來到<愛尬聊_百科全書>了一個神奇的世界。
林吟3354號,2018年夏天,回龍觀醫院

提到精神病院,普通人可能會想到一個可怕的符號。
去回龍觀之前,我也聽到了很多傳聞。比如不能站在空地上,就必須背靠著墻,保證前面有人能看到你,防止病人突然沖過去。
但畢竟我是學心理咨詢的。我對這些東西比較感興趣,時間也比較充裕,所以去過開放式病房和封閉式病房。
精神病醫院病房分為封閉式病房和開放式病房。開放式病房的管理要寬松得多。患者意識比較清醒,家屬可以陪護。患者可以在病房內自由活動和使用手機、電腦,需要在醫生允許的情況下外出辦事,與我們平時所了解的綜合醫院的病房基本相同。

封閉式病房,住著重癥精神病人。
在那里,每個病房都有多帶帶的大門,24小時鎖著。工作人員進出病房時應立即上鎖并再次檢查。病房的大門就像一條生死線,醫護人員會對病人接近大門的意圖或行為特別敏感和警惕,因為像闖大門這樣的事情確實時有發生。
封閉式病房的病人一般更嚴重。我對他們的第一印象真的是“好不好”。
在晨間查房時,你會看到發作期的病人邊跳舞邊唱《一草一木》;還有人打旁邊的床,對著空氣說話。每個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.有的人20多歲就開始生病,現在可能已經四五十歲了。
在第一周,他們突然襲擊的場景會給我很大的情感沖擊。有時候病人控制不了自己,需要護士把他綁在床上。
人家不想傷害他,但是又怕自己被傷害,你知道嗎?這確實是一個“沖突”的場景,盡管他沒有與任何人對抗。
去男病房更嚇人,因為男病房里都是紳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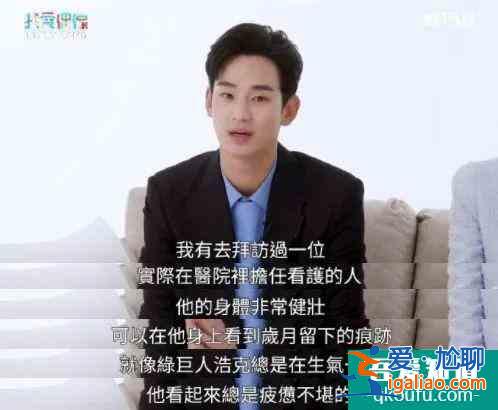
然而,在熟悉了病人之后,有跡象表明任何人都即將發作。比如你說話有點迷糊,跑進跑出——,他們說“XX又不好了”。他們用的專業詞是“壞”。
聽起來很嚇人,但醫生比較冷靜。后來呆了很久,也就淡定了。
除了生病的病人,我不會太害怕他們。我可以和任何有意識,能正常說話的人說話。
其實只是很普通的聊天。聽聽他們的喜怒哀樂,或者吐槽一下父母。哪怕此刻他的心情稍微好了一點,也是很可貴的。

我作為心理咨詢師,覺得挺難受、也挺難以處理的一個部分,是患者在病房里那種孤獨的狀態。
你看現在這個時代了,也不能讓他們把手機帶進去。一個病房里60個病人,只有1個公共電話,每天中午輪流排隊打,每個人只能打三分鐘。整體就是一個非常單調枯燥、與世隔絕的生活。
關系、陪伴對康復是很重要的因素。但在封閉病房的環境下,這是兩難的事情。
有時候,精神病真的是另一種意義上的“絕癥”,就是一種生活的絕望感覺。他們可能會反復發作,帶病生活。
說一句莊嚴的話,人最寶貴的就是相信有希望。在困境面前,你通過所做的每一個選擇來定義自己是什么樣的人。我覺得,Possibility這個詞太美麗了。沒有可能性,是對一個人最大的審判。

去精神病院的病人,其實已經不在我們的工作范圍了。對于處在發作期的病人,心理咨詢很難有什么實際幫助。
所以我其實很感謝最開始告知我們:這是個見習,不是實習,不是要求你來做些什么,你也做不了些什么,定位非常明確。我覺得這對心理咨詢師的職業是一個很大的保護。
——岳也,2012年夏天,北京安定醫院
去精神病院見習,是北大心理系研究生的受訓項目。2012年暑假,我剛剛讀完研一,就和其他3個同學一起,像個小分隊一樣去了安定醫院。
8年前,我覺得精神病院人好多,床位也很有限。
安定沒有回龍觀那么大,環境也比較老式,是那種綠色的墻和鐵門。醫院里按照不同的嚴重程度和診斷分了十幾個病房,一些社會功能好的病房不封閉,一些是封閉(也就是進出上鎖)的。

在病區印象很深的患者,是個有性創傷的年輕女性。
她總是講很多鬼怪故事,告訴我們魔鬼昨天又對她做了什么,“我被魔鬼控制了、我被魔鬼侵犯了”!還有非常多的強迫癥狀。
我當時很被觸動的是,她遭遇過事實上的性侵和家暴,包括父母的早期分離。
她的語言體系雖然難以理解,但你會發現,那些奇怪的語言表達跟情感狀態是匹配的。那樣的病人,通常是因為經過非常深的創傷,讓生活太難以承受和維持了。

在整個見習期間,讓我感覺非常震撼的,是醫生的快速診斷能力。
跟患者聊天的時候,醫生會進入到他們的故事里,使用他們所用的語言。比如問一個妄想的病人:“你昨晚又見到了誰”?問的時候好像云淡風輕,問題都非常簡單,但他們可以馬上從中評估出病人的狀態。
還有他們對待病人的方式。
好多年前,有個青春期的躁狂癥病人,她喜歡上一個特別帥的醫生,然后會對醫生有很多性的表達,比如直接過去要抱醫生之類。她這個行為,其實會被很多其他的病人取笑。
我記得當時醫生是抓住了她的雙手,沒有讓她真的抱上來,比較溫柔拒絕了她,沒有羞辱的那種感覺。對,又溫柔又有邊界,然后使用病人的語言跟她回應。我會記得那種感受,是特別溫柔的。

病人的表現真是豐富多彩。他們跟一般的來訪有區別,但不會像我之前想的那樣好像一個鴻溝、正常人和非正常人的那種區別。不是,他們有點像一個連續譜,其實每個人都是一個連續譜。
從這個角度看,當他們出現癥狀的時候,只不過是離正態分布偏離了一點點。我覺得人的復雜性這件事情,真不是你的標準能夠概括。
——周正朗,2018年夏天,北京回龍觀醫院
我是自己跟醫院約的見習。因為在成為咨詢師的過程中,其實有一些困惑。
當時我還是很新的新手,會接到一些來訪者有精神科診斷。所以我好奇,他們在什么情況下需要得到一個診斷?他們在精神病院會受到什么待遇?雖然我所接受的培訓會提到這一塊,但是教的很理論。
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回龍觀醫院。他們有個院子,感覺特別老派,有那種80年代的老單位的感覺。
剛一進去,其實氣氛特別祥和。一個小花圃,然后旁邊是有點老式的樓。有一些病房是封閉的,病人只能在固定時間出來活動,三三兩兩的。

我去的是開放病房,接觸的是成人和青少年的神經癥病人。如果不是穿著病服的話,他們看上去其實和普通人差不多。
我對一個有躁郁癥的孩子印象很深。她長得好看,有點像《隱秘的角落》里的普普。有天早上她突然情緒崩潰,說想要出院,然后瘋狂地哭。
可能是因為咨詢師接的來訪,一般都呈現出社會功能比較好的樣子。跟他們的交流,會隨著一對一的探索,慢慢呈現出情感的流露。那不是一個很突然的過程。
而那個小女孩的崩潰是突然的,沒有任何征兆(可能是因為我對她沒有深入了解)。跟平常熱情開朗、呼朋引伴的樣子反差也實在很大。

另外,雖然醫生對于病人都有一些職業化的套路,但其實都是關心的。
有的時候,醫生看起來很冷漠,臉一板挺冷酷的,但我覺得他們是為了工作能夠持續進行下去,才需要有一點冷漠的感覺。
早上門診量很大,病人情緒強度也大,許多人滔滔不絕。如果卷入的太多,對醫生來講是非常耗竭的事情。
病人能夠感覺到大夫的善意。一些病人因為住的時間長,家屬、病人、醫生之間互相都很熟悉,經常會進行談話、溝通。雖然不算是非常嚴格的治療,但會覺得他們的家庭結構里面的那些壓力,有了一個往外宣泄的出口。

我之前對有診斷的來訪有顧慮。因為有些來訪的抑郁癥狀非常明顯,他已經喪失對話的意愿,沉浸在情緒里頭重復說一些螺旋話,甚至有輕生念頭。
這些人可能會循環地發病,如果沒有進行任何藥物控制的話,每一次都可能會比上一次更嚴重。純靠咨詢師來打撈,壓力非常大。
但去了醫院以后就沒有這種感覺。他們跟一般的來訪有區別,但不是好像一個鴻溝一樣,正常人和非正常人的那種區別。
藥物可以從化學的角度幫到他,讓他更容易從談話治療中獲益。

“無力感”、“有限性”。每個受訪的咨詢師都提到了這些方面。
心理咨詢常說,要轉化創傷、轉化苦難。“但心理咨詢的來訪者常常是相對正常、有起碼的社會功能的。在人際和人格上一些問題,我們都要花很長的時間去轉化。但精神病院里的這些長期、嚴重的苦難,你會覺得好難轉化,這些苦難就像一座山。”林蔭說。
她覺得,對精神病人由來已久的“污名化”,也是一種對“無力”的反應。人們害怕自己掉到界限的那邊,所以要強調我跟他們不一樣,作出二元對立的一種防御性反應。
陶勇醫生最近有一段采訪很出名。他說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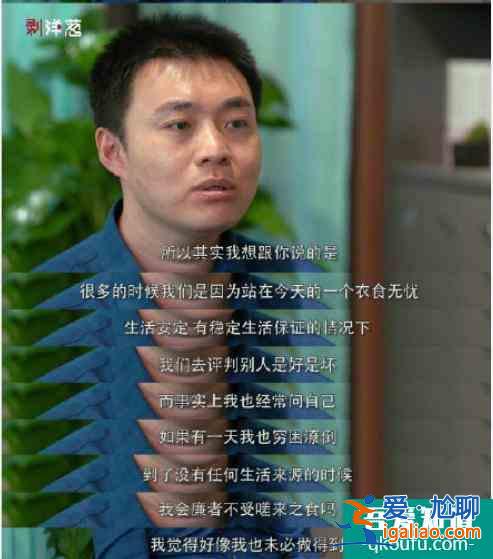
“很多時候我們是因為站在今天的一個衣食無憂、生活安定、有穩定生活保證的情況下,我們去評判別人是好是壞。而事實上我也經常問自己,如果有一天我也窮困潦倒,到了沒有任何生活來源的時候,我會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嗎?我覺得好像我也未必做到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