兒子被圍毆 給打人者處分是底線?

曾經有報道說,一個60人的班級被分成了兩個“國家”。
一邊是經常打人的學生,一邊是其他可能被打的學生。從一年級到三年級,云南西雙版納某小學的班級里,欺凌事件時有發生。家長很生氣,但大多在老師的調解下很有耐心。有些人為了避免欺負自己的孩子,默許自己加入一個打人的“國家”。
母親的加入改變了一切。蘇英蘭是上海一家單位的主管。得知兒子被圍攻后,她迅速飛回家,幾天內熟悉了相關法律法規,逐一聯系了其他被打學生的家屬,并發起了反對校園暴力的聯合聲明。幾經與學校交涉,最終,學校同意對打人的學生進行處罰。
這不是一個讓壞孩子受到最嚴厲懲罰的故事。為了減少對班主任和學校的影響,蘇英蘭沒有選擇報警,也沒有選擇向上級報告,但她還是取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。
被欺負后,10歲的兒子對如何面對和處理暴力同學感到害怕和猶豫。但他可以肯定,道歉是沒有用的,暴力還會再發生。這一次,蘇英蘭希望孩子們能和自己一起面對這件事:“你愿意陪媽媽一起戰斗嗎?”
“我愿意。”兒子說。
這場戰斗也許并不完美,但她想和孩子一起尋找出路,尋找面對校園欺凌時除了逃避和忍耐之外的另一條路。
媽媽的計劃
2022年12月,下午5點,蘇英蘭正在上海一家公司開會。大家都在和風投公司討論資本進入行業的模式,她卻再也沒有心情聽了。她雙手顫抖,買了最快回西雙版納的機票。
幾分鐘前,她接到了丈夫林浩的電話。初三的兒子小藝在操場被7個同學打了。電話那頭的丈夫氣得哽咽,甚至想到了和對方父母“同歸于盡”。
我們離婚,孩子判給你。蘇英蘭驚呆了。“為什么?”這是林浩的沖動策略。如果與其他家長發生沖突,他將自己承擔全部責任。
“我不會回來了。你要的是什么樣的婚姻?”“我單方面宣布離婚。”“有用嗎?你知道離婚的程序嗎?”林浩沒想那么多。“我去了。”蘇英蘭趕緊給表哥打電話,讓他抱著丈夫。
蘇英蘭知道丈夫的怒火從何而來。初中的時候,林浩也遇到過校園欺凌。當時他成績很好,是個外地人。他的同學經常打他,搶他的錢。告訴老師也沒用,家長也不管。林浩想過退學。為了保護自己,他不得不加入校外的壞男孩團體,逃課,成為一名更具攻擊性的斗士,但他的成績從此受到影響。
上三年級的兒子前兩天睡覺前說要轉學的時候,林浩的神經一下子緊張起來。在小藝的描述中,周四體育課自由活動時間,以陳子航為首的7名同學突然追上他,對他拳打腳踢。兩個密友上來幫忙,一起被打。林浩馬上檢查了孩子的身體,沒有明顯的傷痕。他稍稍松了口氣。
從上海回西雙版納老家最快也要17個小時。打完最后一個電話,回到會議桌的蘇英蘭向朋友要了一張白紙,開始寫思維導圖。她忽略了自己的狀態,顯然沒有參加會議。
繪制“腦圖”是業務主管解決問題的方法。面對這個特殊的“項目”,她在A4紙的右上角寫下了自己想要的結果:第一,小伊的心理狀況恢復健康;<愛尬聊_創建詞條>第二,懲罰打人的孩子;第三,法治進學校。
圍繞目標,她開始細化分支路徑。她需要了解反欺凌法律法規,了解事件真相,了解班里是否還有其他孩子被欺凌。她打算和學校協商三次。第一次學校會給她初步的解釋,第二次會給她初步的解決方案。v星人
“前三秒寫個腦圖,第四秒開始行動。”蘇英蘭遇到問題一直都是這樣。但是最近一趟回家的航班是第二天早上,她擔心在這個空檔里事情會發生變化。
在苦難中,她開始盡她所能。她咨詢了律師,聯系了媒體,動員身邊的同事收集了所有與校園暴力有關的信息,也看了其他被欺負孩子的母親分享的經歷。“他們拼命給我發東西,我就努力消化。”
還有一些讓蘇英蘭哭笑不得的熱心幫助。一個快遞公司的朋友聽說了小易,說要動員所有快遞員在學校拉橫幅。另一個山東的同事說:“你等我讓一群小男生干他們。”蘇英蘭曾經想過把后續的經歷做成小視頻放到網上。一位導演朋友提醒她不要這樣做。“不是所有人都會認為你做的是對的。”
蘇英蘭預言,這將是一個長期的“工程”。出發前,她收拾了好幾天的行李。

慣用暴力
鄭書怡的母親也聽女兒說起過這件事。2022年12月1日,鄭書怡放學回家,像往常一樣在班上分享這個消息。“陳子航演了個小逃。”亦舒的母親沒有多想,認為這又是一次“普通的毆打”。
她知道陳子航是班上最調皮的孩子,女兒每天總會分享他:“陳子航又打人了”、“把xxx打死了”、“把老師的葫蘆絲弄斷了”、“跟國際手勢比”,女兒漸漸對此習以為常。
有家長形容陳子航是一顆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,隨時隨地都有可能來襲。只有班主任才能守規矩。很多家長告訴孩子“離他遠點”。擔心女兒性格內向,受欺負不敢說出來,鄭書怡的媽媽會換一種說法,問:“你一個人上樓梯的時候,突然遇到他,就你們兩個。你會害怕嗎?”看到女兒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恐懼,她暫時松了一口氣。
平時在校門口接孩子,出來鼻青臉腫的,家長一看就明白了,“除非你跟陳子航玩得太好,不然大部分男同學都被打了。”鄭書怡的母親說。
蘇英蘭并不清楚這些情況。她常年在外工作,丈夫在家照顧兩個孩子。為了讓妻子少操心,林浩大多報喜不報憂。下了飛機,蘇英蘭立刻開始進行她的“腦圖”。她和小藝在房間里待了三個小時,稍微問了一下這三年來的情況。
一二年級的時候,小藝被一些同學潑墨水,弄壞文具,有時還被陳子航打。每次他向班主任投訴,欺負他的同學都被叫到辦公室道歉,但他很快就恢復了。從三年級開始,幾個欺負他的同學開始聚集在一起,以陳子航為首,在老師無故不在的情況下,在體育課的空閑時間打他。小藝說,這學期幾乎每節課都會打體育課。林浩回憶,之前小藝提過一次,不想去上籃球課,但他沒有具體說為什么,當時也沒在意。
還有一些事情,小易不確定是不是在欺負自己,一直沒有主動說。每次在衛生間門口遇到陳子航,小怡都會被扒光下體。“很多同學都這樣做過。”陳子航還會當著同學的面罵他,跟他比中指,“罵的很臟的那種”,這是他學不會的。小藝重復說想轉學。他害怕被打,擔心其他同學看他的眼光。就連上廁所都成了一件很煩人的事情。
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,蘇英蘭了解到,這些行為分別對應著“身體欺負”、“言語欺負”和“關系欺負”。她把小怡的經歷記錄下來,歸類成文件,準備后續和學校交涉。
晚上,蘇英蘭和丈夫約好了班主任。對方答應會向保衛處反映,并聯系打人同學和家長,了解清楚此事。小怡躲在蘇英蘭身邊,神情十分緊張,聲音克制著顫抖。班主任安慰他:“你明天還是會來學校的,大方一點。如果你有什么事,舉手對老師說,“沒什么,給老師一個微笑。”肖逸勉強笑了笑。
林浩也漸漸冷靜下來,安慰妻子不會再沖動了。他責怪自己沒有照顧好孩子。他特意加入了班級家委會,負責組織體育活動。事實上,他想更多地關注兒童的狀況。“沒想到會這樣。”
第二天放學回來,蘇英蘭問小依:“今天過得怎么樣?”“我去了語文數學什么的。”“怎么樣?”“只是上課。”“你害怕嗎?”小藝看著媽媽,很“害怕”。小藝說上課沒事。他離陳子航的座位很遠,但是下課了,上廁所的時候,他很害怕。還好班主任叫其他同學跟他一起去。
“如果他們向你道歉,你會接受嗎?”小藝說:“媽媽,我真的不相信他們的道歉。他們已經道歉很多次了。”然后我回房間做作業。蘇英蘭感到很不舒服。那兩個晚上,小易晚上會叫,但走過去拍拍他,又睡著了,早上起來也不記得了。
疫情在西雙版納蔓延,兩天沒上課。聽到家里要上網上課,小藝笑了。“太好了!”其他時候,他話不多。蘇英蘭咨詢了一位心理學教授,他建議鼓勵孩子表達和接受自己的恐懼,放松。那段時間,蘇英蘭和林浩經常帶著孩子出去散步,一起做游戲,一起看動畫片。
小易也頻頻提出要學跆拳道。陳子航是個壯漢,也學跆拳道。蘇英蘭說,你看媽媽的胳膊,那么瘦,一點肌肉都沒有,松松垮垮的。你看爸爸,他很弱,但是我們沒有力量嗎?她擔心小依會覺得只有暴力才能保護自己,決定帶他參與這件事的解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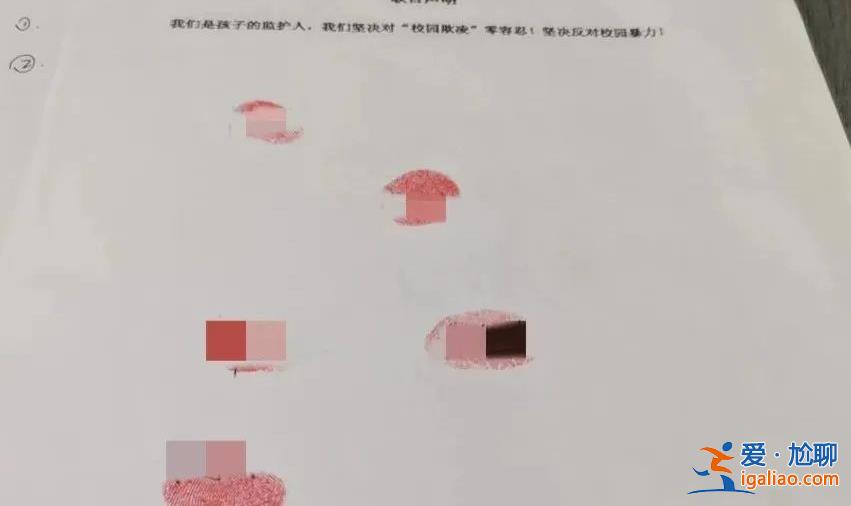
兩個“國家”
班主任聯系打人學生家長后,蘇英蘭和林浩陸續接到他們的道歉電話。
家長對欺凌的描述從“調皮”到“動一動”再到“踢幾腳”,不一而足。一位父親解釋說,“他們這個年紀,平時可能交流不暢。”蘇英蘭對這種弱化欺凌的措辭感到憤怒,并立即普及了欺凌的定義。“xx爸,欺負分為主動欺負和反應欺負。反應性欺負是指欺負者事先被被欺負者挑起或激怒,但都是欺負行為。”在研究數據之前,她原本認為反應性欺負是挑釁者的錯。
最讓蘇英蘭哭笑不得的是,一個家長什么都不懂,一上來就說對不起,還念錯了小藝的名字。“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,所以老師讓我們道歉。”另一位母親說,她的孩子不知道被陳子航打了多少次。
蘇英蘭意識到這件事不僅僅是個例。她向其他家長詢問其他被欺負過的孩子的情況,按照班級群的聯系方式一個個打電話。她驚訝地發現,自己的情況其實很輕。
一年級的時候,王克誠被陳子航推下樓梯。剛從幼兒園畢業,王克誠的媽媽以為孩子只是有點調皮,但是二年級的時候,王克誠被打了好幾天,有時候在肚子里,有時候在心里,晚上睡覺的時候突然哭出來。
有一次放學,王克誠的媽媽見到陳子航說:“不許你再打我們王克誠,不然我報警。”陳子航沒說什么。一到家,她就接到了陳子航父親態度惡劣的電話,說她威脅他的孩子。
王克成的媽媽想過報警,但班主任說會處理好。考慮到警方可能會對學校造成影響,她最終沒有追究。她知道班主任很負責。只要有同學被欺負,她都會處理。如果嚴重,她會繼續向保衛處反映,要求雙方家長都去學校,但最后都以道歉告終。
從三年級開始,很多孩子發現以前不那么差的同學開始加入陳子航,形成了一個四五人的小團體。鄭書怡說,以前很少有人和陳子航一起玩,但現在“他們已經成了一個國家”鄭書怡的媽媽聽到一位家長說:“我的孩子說:我們是兄弟,所以他不會打我。”大家似乎已經形成共識,只要加入陳子航,就不會被欺負。
蘇英蘭聯系了十幾個家庭,希望簽署反對校園暴力的聯名信,呼吁學校重視,但并不順利。
大部分家長擔心學校會認為他們在搗亂,孩子以后可能會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有家長認為蘇英蘭只是想讓家里的事更有影響力。蘇英蘭很郁悶,覺得這些家長有些可憐。“我明明被欺負了,卻不敢說,連爸爸都不敢說。”她理解父母的擔憂。當地好的小學不多,家長都很珍惜進這個學校的機會。
當我第一次接到蘇英蘭的電話時,鄭書怡的母親也很驚訝。“這么大?”但得知她是為了全班著想,她決定站出來支持她。女兒雖然沒被欺負過,但是聽說太多同學被打了,她不希望女兒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。“既然學校沒有妥善處理,肯定有家長來處理。我覺得她挺英雄的。”
最后,三家簽署了反對校園暴力的聯名信,并按下了手印。蘇英蘭原本想呼吁學校加強反校園欺凌科普教育,但因為怕影響其他家庭,沒有拿出來。
三次談判
事發兩天后,學校聯系打人學生家長了解情況,并第一時間約見蘇英蘭。
她做了充分的準備,提前熟悉了《西雙版納州加強中小學欺凌綜合治理實施方案》和《公安機關可以訓誡未成年人的6種情形》,了解到原則上學校要在啟動調查處理程序的10天內完成調查。她也熟悉了法治副校長的崗位職責,也翻看了學校微信官方賬號,發現學校之前關于反欺凌的科普活動非常有限,而且不是面向各個年級的學生。
一名代表學校的老師表示,打人的幾名學生已經承認了被圍毆的情況,與小藝的描述相差不大。蘇英蘭覺得學校在積極解決問題,希望和他們站在統一戰線。
她分析,校園霸凌最擔心的是名譽受損。蘇英蘭很有談判技巧。她決定從這里找一個突破點。“我知道創新的績效指標對評估工作非常有益。這個反欺凌的東西可以成為你的創新作品之一,推成典型案例。”
她也給學校施加了一些壓力,說如果向上反映,可能會對學校的評價產生影響。我也接觸了一些媒體。
為了避免被最小化,她還要求代表學校的老師簽字,保證“學校會公正公開地處理整個事件”,并按上手印。
根據學校的反饋,蘇英蘭評估哪一步更合適。讓陳子航轉學是大多數家長的訴求,但老師表示,根據《義務教育法》的規定,學校無權開除學生或變相開除。蘇英蘭知道這不現實。如果她做不到,會被學校為難。她決定后退一步。“我相信給處分不過分。”
蘇英蘭引用《實施方案》:“對于反復發生的一般欺凌事件,學校在對欺凌者進行批評教育的同時,可以根據具體情節和危害程度給予紀律處分;學校應該盡快聯系
給予陳子航處分是蘇英蘭的底線,也是區別以往處理方式的界限。她問小藝,“如果陳子航沒有轉學,如果他們當著全校的面給你道歉,寫保證書,你會相信嗎?”小藝馬上回答:“我不信,因為告訴老師也不管用,保證也沒用。”
對于學校來說,做出出具蓋章處罰和情況說明的決定并不容易。蘇英蘭說,后來老師打電話來商量,說如果懲罰太嚴厲,小怡以后可能和其他孩子相處不好。蘇英蘭覺得這些話看似有道理,其實是個偽命題。“如果打人者在班里被處理夠了,你覺得其他同學會怎么看待這件事?”我們走正道,走出來,后面的人也會跟著走。一個同學怎么能不和他玩呢?應該離他比較近。"
老師還建議陳子航的父母通過賠償的方式解決問題。蘇英蘭拒絕了。“如果賠錢道歉,一切都可以解決。處罰有商量的余地嗎?”
蘇英蘭和林浩原本希望報警,即使不能做出實質性處罰,也讓警察在學校出現一小段時間。前一天,她去王克成家了解情況時,提到可能會有警察去學校調查。王克誠突然變得開心起來。“警察叔叔真的會來嗎?”是警察叔叔嗎?”蘇英蘭安慰小怡的時候,也下意識的說,“沒事,有老師,有父母,有警察叔叔。"
但是學校不想把事件擴散到校外。蘇英蘭也嘗試從學校和老師的角度去思考。《實施方案》中提到,如果發生欺凌事件,分管法治教育的副校長和班主任負有直接責任,治理情況也將納入文明校園創建和班主任考核。
班主任是小怡一年級的時候從農村調過來的。他也有一個孩子,放學后經常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林浩和班主任有很多接觸。他明顯看到班主任比一年級大很多,看起來總是很疲憊。他覺得班主任沒做錯什么,不想讓她一起受罰。“好人也需要互相保護吧?”林浩擔心,如果班主任調走,“這輩子好老師會毀了嗎?”她以后會不會不那么負責?會有更多的孩子受到影響嗎?“蘇英蘭也認為,事先善良,然后改正是必不可少的。
雙方各退一步。最終,學校接受了蘇英蘭的要求:給予陳子航較重處分,對其他打人的同學給予通報批評,對小怡被打事件進行說明,并在學校開展反欺凌科普活動。
學校發給他們的第一份情況說明書只有一份書面總結。蘇英蘭覺得不行,要求帶上學校的信箋和公章重寫。她知道這樣的文件在自己手里只是一紙空文,但對學校來說,就像懸在她頭上的一把劍,對陳子航來說,就像孫悟空的魔咒。學校還說,如果再出事,他們會幫忙勸陳子航退學。

和媽媽打這場仗。
小易幼兒園畢業的時候,老師讓每個家長給孩子寫一封信,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讀出來。很多家長寫的都是感謝老師媽媽愛你之類的套路內容。蘇穎蘭的題目是《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》,“分開是為了下次更好的聚在一起。如果好起來了,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團聚。”
這樣的家庭模式在班里很少見。爸爸是組里接孩子的幾個男的。媽媽常年在外工作,不忙的時候回家一段時間。她對孩子的愛在不斷的分離和團聚中流淌。
蘇英蘭父母很早就離婚,母親看重事業,經常去外地出差。保姆照顧她的基本生活。雖然我身邊沒有人陪,但是只要媽媽需要,她一定會回來的。媽媽從來不和她說哄孩子的事,還說很多大人世界的事。
蘇英蘭和蕭藝也處于類似的相處模式。他們會像朋友一樣討論各種問題。做項目遇到困難的時候,小藝看到媽媽很頭疼,就問:“你在擔心什么?”蘇英蘭如實相告,小依也常常給出一些天馬行空的回答,“可以……”
起初,小藝聽說爸爸媽媽要找老師和副校長。他擔心投訴后可能會被打得更狠。蘇英蘭告訴小依,逃避解決不了任何事情。只有面對恐懼,我們才能快速成長,保護自己。“你愿意站出來陪媽媽打這場仗嗎?”我知道。
每次和學校對話結束,蘇英蘭都會第一時間分享給小伊。“過來,我向你匯報一下我的工作。”她省略了具體的談判過程,用一個孩子能聽懂的語言總結事情。
隨著談話的進展,小藝覺得這次的處理方式似乎和以前不一樣了。之前結束了一次,現在有第二次,采訪對象上升到了法治副院長的級別。蘇英蘭看了,心里高興。小易很害羞,幸福的表情就是露出笑容,走路的時候蹦蹦跳跳。到第三遍的時候,小藝已經沒有反應了,只是“哦”了一聲,重點就跳到擔心背古詩上了。
2月5日,第三學期的第一天,她發現小怡不想像以前一樣吃早飯了。他收拾東西比姐姐還快,催他“快點”。
本周班里開了一次班會,主題是預防校園欺凌。陳子航和幾個打人的同學當眾向小毅道歉。保衛處處長代表學校在全班宣讀了對陳子航的處分決定。班主任打電話給蘇英蘭,說這學期班里的孩子好多了。放學后,鄭書怡沒有帶回陳子航被打的消息。
蘇英蘭問小依:“他們向你道歉的時候,你是什么感覺?”她擔心聽到“開心”的回答,可能是說小怡感覺比他們好,也擔心聽到“害怕”。小伊說:“我沒什么感覺。”蘇英蘭放下心來。
小藝好像原諒了一些打人的同學。林浩送他去學校的時候,看見小藝叫著他一個同學的名字,一起走進了學校。小藝說,陳子航再也沒有欺負過他,但是上廁所的時候,他會習慣性的避開陳子航。陳子航去了,他就不去了。
事發兩個月后,蘇英蘭的“項目”即將結束。
蘇英蘭在與小怡和她姐姐的聊天中發現,小怡對自己在學校被欺負的事情直言不諱。她想她也許能買張票回上海。
